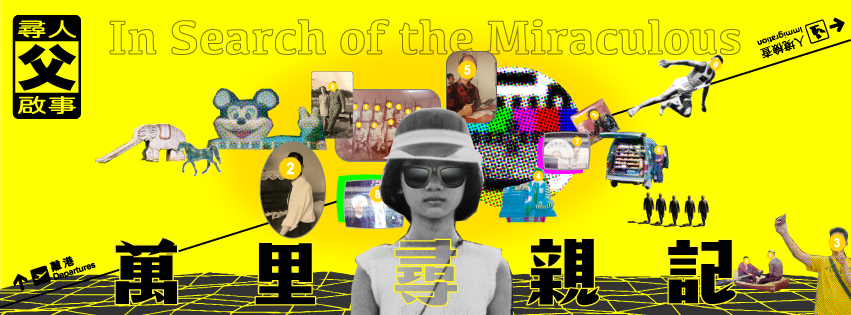圖版來源:再拒劇團粉絲專頁
文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/陳泰松
好聲音?當然不必了
關於《春醒》─再拒劇團年度音樂劇
個人很喜歡這齣音樂劇,演得好,演員傑出,充滿活力,台詞自然流暢,簡單講,態度有真梗而不耍弄,且這裡有好的文學與表達的真誠,不像某些老成持重的劇碼,說是為了表現生命深度,對白與陳述的語詞卻造作扭捏,就算那是經典文學的挪用,只不過是要揣摩或體現文本的精神向度而已,但通常只是語調的喧染效果,徒具形式的表面軀殼。
要把《春醒》擺在什麼位置?
先不管音樂劇,《春醒》是搖滾樂的演出如何!若是這樣,它可贏過台灣現今各種(包括大咖或不知道什麼咖,唱什麼藝術家之類)的流行音樂。比起歌詞無聊到只會靠韻腳的填詞,假裝出自己有思想與感覺內容的歌手或等等,《春醒》有內涵許多,坦誠且有趣許多。單看流行音樂詞句之蒼白,就不用去理它們是沒救的文化狀態。坦白講,通俗流行不一定就必須易懂,讓人沒心情負擔的好玩消費品。有這種念頭的人其實是無知的受害者,是被特定的媒體工具所洗腦,以至於把商業的感性原本是來自異端的發想,卻把自我縮限在跟班的世界裏,它的對照組便是因襲既定市場,以穩賺為保守準則的意識形態,若說還有什麼創意,也只不過粉妝既定事物,看似風格化的趣味衍生,不外乎是僵在既定框架內,是生產被主流體制內化或植入的一種自我審查,好像遭到它以微細管插入的思維管控。
但難懂的事情有那麼搞嗎? ——其實只要有心並不難。《春醒》的演出給出簡單的答案:節奏、旋律與貝斯。就是說,《春醒》的搖滾樂很容易聽,人想要嗨也容易,換句話,樂音跟時下流行的沒有什麼兩樣,不搞怪或搞怪(隨你認定),都是一般得很。然而,只要讀它的歌詞字幕便可明瞭它的殊異。既然如此,再拒劇團以其樂音的通俗,何不把它的《春醒》弄到小巨蛋或其他演唱會場演出呢?

圖版來源:再拒劇團粉絲專頁,攝影:唐健哲
理由也很簡單,再拒劇團不是樂團!它期許在劇場裏,不在搖滾樂應有的展演空間脈絡裏去引發美學擾動的能量;不過,這是就樂音來講,若以歌詞的意念來說,《春醒》何不去串周杰倫、蔡依林、阿妹、五月天乃至張震嶽或伍佰等老老少少、有名無名繁族不及備載的場子!且讓我們看看彼此路線的碰撞,在如此緊縮的空間中彼此如何肉搏回應。當然,只在自己所屬的劇場空間作演出,哪裡都不去也可;那麼,《春醒》的樂音製作便要有所推敲,因為如前面說的,不夠反叛,因而浪費了劇中的性愛戲擬,太過溫馴,因而坐實了展現青春的獻祭,所以有耽溺於既有政經體制的美學之嫌。這或許就是《春醒》的話語實踐的曖昧處吧。讓我們重彈老調牙:「形式」本身並不是無辜的,它包藏意識形態的心思並不比它所要講述的內容還少,甚至它才是讓事情見真章的所在。換句話,「內容」往往更是一種用來掩飾的形式,因而「形式」是暴露真相的語誤,是真相不經意的露餡!這也是為何最好以符碼的說法來代替“形式內容”的二元論。
至於《春醒》是講什麼呢?
但換個角度來說,“要成為怎樣的大人”不是《春醒》感興趣的轉型,而是“要成為怎樣的青少年”!不過,這裡沒講,而是一段還沒成為大人的就學期的困頓青少年,隱喻是:雞,正如台詞說的,且還提到日後長大也仍會是雞,也就是說,被剝削的存在者。這不就衝破了《春醒》所佈建的僵化二元論,因為管控生命政治學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大人與青少年的世代之間,而是散佈在各個世代自身內部強者與弱者之間。這不是說,二元對立論不見了,而是時時刻刻它表現在差異化的流變過程之中;簡單講,會吃雞的,不僅會是比你大的人,跟你同樣大的也會,只要他∕她比你強。這是《春醒》的敘事侷限嗎?不全然是,因為它只處理這個區塊--青少年與大人--就足以引起共鳴了。這讓人想到一個問題:身為大人們的你,若是不同於操控者,譬如說,你是進步份子,或左派信徒,或不掛名的開明人士等等,應去跟他們(不僅是青少年而已)結盟?省省吧,與其去當個精神導師,倒不如去努力替他們提供可以發揮自我的資源與平台,為他們疏通社會管道與串聯領域的隔閡,頂多是“精神工具”便適可而止。
(轉載自Artalks)